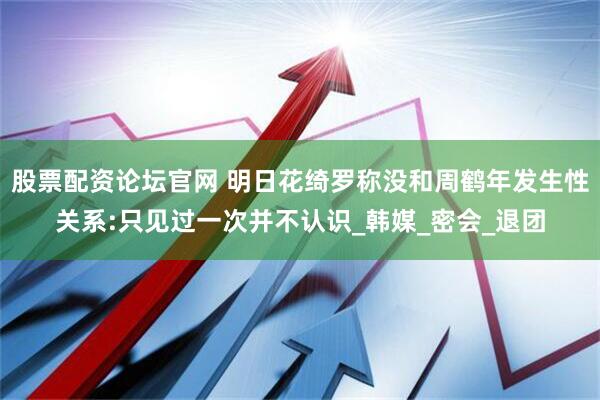“2023年7月股票配资论坛官网,在高空一万米,机长提醒:‘各位旅客,前方即将降落若尔盖机场。’”一句平常的广播,把我拉回到那个被先辈称作“吃人”的地方。客舱里灯光柔和,咖啡香淡淡飘散,很难想象窗外那片碧绿,曾经让一支钢铁部队付出一万六千条生命的代价。
飞机落地只用短短几十分钟,可在八十多年前,中央红军要穿越同一片草地却花了七天。草原上如今有国道、有加油站,导航语音清晰响亮,牧民开着皮卡兜售酥油茶。路标上写着“海拔3400米”,数字很冷静,却不足以说明那里的稀薄空气、低温和湿气曾怎样无情地蚕食体力。

当地藏族老人告诉我,他们的长辈至今仍把那段时间称作“黑色七日”。在老人们的口述里,草地无边无际,连一块石头都稀罕;脚下的泥炭层像张巨大的陷阱,静静等候。稍有不慎,人连枪带包一起没入泥塘,连涟漪都来不及泛起。
时间拨回1935年6月。懋功会师刚结束,按中央原本的计划,红军希望北出松潘直入甘肃。倘若张国焘能够同心同德,或许就没有后来的“死亡禁区”一说。然而现实并不给假设留下空隙。拖延、分歧、敌军合围,把大部队逼向若尔盖。毛泽东无奈下令:穿草地。
这片面积超过三万平方公里的高原沼泽,温度常年只有个位数。白天水汽升腾,夜里寒风如刀。红军进草地前,每人只勉强筹到十来斤青稞面。可高强度行军日耗体能惊人,干粮往往两三天就见底。无补给、无退路,饿肚子成了常态。
饥饿尚可用意志咬牙对付,更可怕的是“脚底的敌人”。许多沼泽看似结实,一脚踏空就再无返回机会。老红军李世焱回忆:一天傍晚,走在前头的通讯员崔华义突然没入淤泥,“像被人拽下去”,同行十几人合力拉扯,绳子几次从手心滑脱,最终只摸到一顶湿漉漉的军帽。

水源同样致命。草地盛产暗河,表层看似清澈,实则富含苷类毒素。卫生员反复叮嘱“能不喝就别喝”,可口渴难耐的战士哪顾得了那么多。一个连的伤员在误饮后出现剧烈腹泻,不到三小时倒下七人,这还不算因失温而昏迷的。
当年的非战斗减员数字,如今仍让军事史研究者心惊。官方档案记载,中央红军过草地七昼夜,减员1.6万人,占长征全部非战斗损失的三成以上。其中绝大多数,是饿死、冻死或陷入泥潭。很少有人战死沙场,却同样壮烈。
困境逼出许多匪夷所思的生存办法。皮带、羊毛毡、甚至缴获的报纸都被煮着吃。有人从牛粪里挑出尚未完全消化的麦粒;也有人把步枪背带切成段,卷成“面条”。“能嚼下去就是好东西”,这是经历者最直接的标准。

巧合的是,就在红军艰难北上之际,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正着手制定第六次“围剿”计划。得知对手冲出若尔盖,他沉默良久,对幕僚说:“他们进了鬼门关还活着出来,这支队伍不好对付。”有时候,承认对手的坚韧,是逼迫自己正视失败的唯一方式。
新中国成立后,若尔盖草原从“此路不通”到“八车道柏油”,用了整整七十年。首先是筑路:1958年,第一支筑路营进场,工兵把钢轨打进冻土,炸药包一轮又一轮。随后是电网与通信:2006年第一根220千伏铁塔在草地上竖起;2014年4G信号覆盖主要牧区;去年5G试点站又亮了红灯。
发展并非单纯“水泥加钢筋”。2010年起,国家投入专项资金恢复湿地生态,植被盖度从不足35%提升至60%以上。科研人员通过分流河道、封育牧场,让昔日“泥炭黑洞”逐渐干爽。曾经吞噬生命的沼泽,如今在游客脚下成了柔软的草甸。
牧民的日子也跟着变了。年轻人会在周末把牦牛肉切好真空包装,载去九曲镇冷链中心;老人守着新修的藏家乐,泡一壶酥油茶,招呼城里朋友听玛曲河的潺潺水声。有人感慨:“祖辈信奉神山神水,如今我信公路与网线。”朴实却不失深意。

游客来到红军长征纪念碑前自拍,也有人在“死亡泥潭”旧址前驻足良久——那片地表已经加固、植绿,旁边立着一块木牌:请勿踏入恢复区。工作人员说,这是为了生态,也是为了历史,“别让脚印把记忆踩浅了”。
若尔盖的夜,风依旧凛冽,只是营地早装上了电暖。抬头看满天星斗,想象当年周恩来、陈赓抬着担架在泥泞中踉跄前行,心里忽然生出难以言说的敬意。草地不再“吃人”,可那段生命与信念冲突出的光芒,始终照在每一个后来者的头顶。
红腾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